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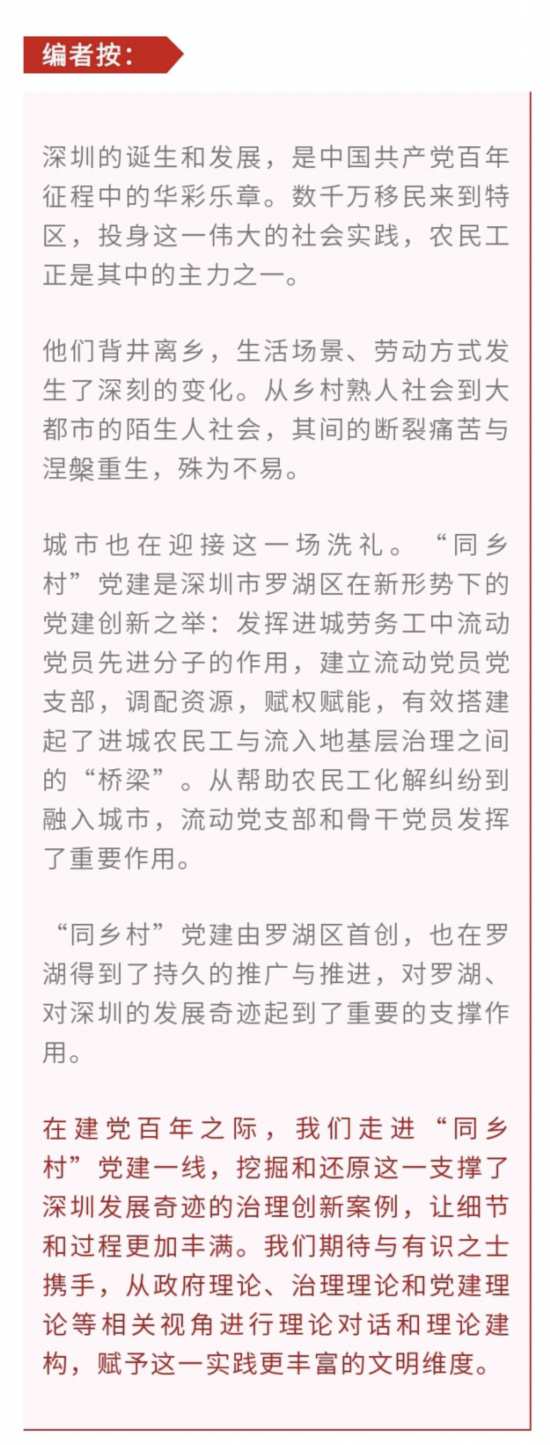

一
我1971年生在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安云乡木龙村。我们村人多田少,每人只有2分田,粮食不够吃,经常挨饿。树皮、草根、地耳,我们小时候都挖着吃过。
我家从我曾爷爷开始,都是村里的干部。我爸当过生产队长、村会记、党支部书记。生产队的牛死了,家家户户都分了肉吃,连孤寡老人都没落下,唯独我家没有。我们三兄弟饿得不行,爸爸只好趁天黑,把几根没人要的牛棒骨偷偷捡回家。骨头早被剔得一干二净,一丝肉都没有。丢进铁罐罐里熬汤,也不见多少油腥。我爸这个人耿直,不懂偏私,他对我影响很大。
我是家里的老大,初中毕业之后,操持家务事。农闲时候,断断续续跟师傅学过一年木工。1990年10月下旬的一天,我正在发小家帮忙修谷仓,同村的魏心兵来了。他长我几岁,已经出去打工了。他问我们,要不要到深圳去做工,老家工资3块钱一天,在深圳有8块钱!我们都被说动了。
爸爸说,你也十七八岁了,该出去闯闯。我连夜收拾行李,爸爸到处借钱,东拼西凑了200元,给我做路费。我和发小一共五个人,第二天一早就出发了。那会根本不晓得深圳在哪里,也没有想象过是什么地方。
坐铁皮火车,加挂车厢,没座位,没窗户。先到陕西、湖北,再到广州,倒了三次车,坐了7天,好不容易来到深圳。
二
刚来是在宝安,二线关的铁丝网外面,住在石棉瓦搭的工棚里。两天后,一个老乡介绍我们去碎石场工作。开山炮炸了,山上都是石头,我们要把石头扛下来,打碎,做成建筑材料。早上6点多起床,7点上班,中午歇一个小时,下午干到6点多天黑,每天10个小时。
我干了半个月,一分钱没拿到,但是管饭。吃得不好,饭里头有碎石子,硌得牙疼,青菜夹起来抖一抖,掉下来好多虫子,紫菜汤里全是水。那时候不想那么多,吃饱就行。一个发小跟我一起去的,他比我聪明些,知道拿不到钱,就少干,或者不干,照样有饭吃。他们总是笑话我,“太实在。”

那会年纪轻,干活虽然累,但体力好啊,睡一觉就恢复了。二线关外跟老家的县城没什么两样,但靠近机场,每天都能看见飞机在很近的地方飞过,觉得很新奇,也很兴奋。
1991年上半年,我去修北环大道竹子林段。每天运沙,铺沙和石子,做水泥沙垫层,晒得像黑炭。说好10块钱一天,做了半年没领到钱,被包工头卷跑了。不知道找谁,也不敢去问,问了又被骗怎么办呢。
当时没想过走,因为这里挣得比老家多太多。一天10块钱,一个月就是两三百块,加班加点能有三四百。1990年10月到1991年12月,我攒了1000块钱寄回家。后来用这笔钱结婚了,给老婆买了十几二十套衣服,还添了很多小物件。当时在村里很有面子,人人都羡慕。
三
1994年,去盖地王大厦,进了吊装班。我从小爬树,从这棵树跳到那棵,不怕高。在空中安装钢结构,就是要胆子大,心细。这活不是人人能做的。那时候和工友坐在横梁的两头,吊在空中转圈都不怕。
一天干9个小时,拿16块钱。吃建筑公司的饭堂,点最便宜的菜,一顿两三块,一天吃饭用8块,能存下8块。钱不多,但我知道盖的是将来亚洲第一高楼,心里面也有自豪感。

项目部就在工地上,我和正式工聊天,有人说,公司给我们的钱不止每天16块,是被克扣了。我们每天要在天上吊着,干最苦、最危险活,不应该只有16块钱。我想找领导,但只认识班长,他是正式工,不为我们说话。吊装班的10个人都是老乡,我跟他们说,这不成,我们不干了,停工!
当时停工可不得了,停一天公司就损失一天。项目的总经理马上就见了我们,在工地上集装箱搭的办公室里。班里10个人去了4个,其中还有和我一起闯深圳的发小魏宗山,我是撑头的。
我跟总经理说,我们的活又累又危险,每天只有16块钱,这不合理。他说不对,公司发给你们是三四十块一天。他当场打电话查是怎么回事,才知道是包工头克扣了。他说:“小魏啊,你们放心,继续干,这个事情我马上给你们处理好。”之后每个月的工资,从几百块一下涨到了一千八到两千,翻了好几倍。
高工资我一个月都没拿到。工资的事情摆平后没几天,我从住的地下室上铺摔下来,手臂脱臼,干不了活了。刚好又是年底,我回了老家。我走的时候,地王才盖到20多层。
魏宗山和他弟弟宗全留了下来,一直把地王盖完,工资涨到了每月五六千块。我这个撑头的,啥也没得。他们经常拿这事笑话我。
四
从农村到城市,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。90年代,刚来到深圳,真是“刘姥姥进大观园”,看什么都新鲜。
打零工的钱都是日结,也有月结的。发了工资,最开心的是叫上两三个老乡,买两瓶酒,再要一碟花生米。酒是百乐啤,七毛钱一瓶,关系好的,就喝百事可乐,一块五一瓶。
那会只要有新来的老乡,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买一瓶可乐。可乐有气,喝下去会冲鼻子,还会打嗝,第一次喝,是很新鲜的事。大家都爱喝,主要还是便宜。
我在深圳拍过第一张照片,在三九大酒店门口。当时很多地方没有建起来,酒店晚上有灯光,有喷泉,环境挺好。我们几个老乡一起,花钱请人家拍。小的5块一张,大的10块。拍了就给父母寄去,让他们看看我,告诉他们我过得挺好的。
到现在我都没进去过锦绣中华、世界之窗,花这个钱我心痛。只去过莲花山、大梅沙,这些地方是不要钱的。但是老乡谈起来,我都说去过,要面子的。
1993年左右,有老板付钱给我,让去证券交易所前面排队,买股票。股票是凭身份证买的,要排队买,人山人海。我不懂咋回事,从早上排到下午,拿回一张纸的凭证,老板就会付排队的工钱,一天10块、15块。我经常想,要是那会我给自己也买上几十股,该多好啊。
五
1997年,我回到老家,没再出来打工。1998年12月,我27岁,当上了村主任,是整个乡里最年轻的。村里办事没钱,我就用家里的钱贴补。当了6年村主任,不但没攒下钱,还欠了1万多外债。
2003年,我爸病了,儿子女儿要上学,样样都要钱。那年7月,我又来到深圳打工,这次一做就是快20年。
2007年6月一天,有人来找我,说是达州驻深办事处的。我累了一天,已经睡下了,被叫起来,有点不情愿。一见面,反问他们:你们说是达州驻深办事处的,有工作证吗?当时的驻深办主任廖清江、副主任蒋洪毅愣住了。一个工作人员出示了工作证,我才相信。
他们是来找党员,准备成立流动党支部的。廖主任后来告诉我,因我问了工作证的事,他们认为我是个讲原则的人,当时就在心里认定要让我当党支部书记了。廖主任现在不在深圳工作了,还常常和别人谈到我,“这是敢查我工作证的人。”
让我当书记,起初我是不干的,当了6年村干部已经够了。一次活动,当时罗湖区的领导把我叫到一边,问我为什么不愿意。我当过基层干部,知道当书记是要付出的,要花很多精力。我说,我爸卧病在床,孩子要上学,我从家里出来才几年,想赚点钱。

他安慰我说:“放心干,支部书记干好了,大家会记住你的。你有什么困难,直接来找我。”那时我什么也不是,只是一个农民工,他能这样和我说话,我心里有点触动,觉得特区的干部没官架子,接地气。
2007年6月14日,我给爸爸打电话,问他的意见。他身体不好,在电话里断断续续地对我说:“可以当,但是要当就一定要当好!”6月15日,罗湖区清水河街道辖区四川达县流动党员党支部成立,我成了书记。
一开始去调解纠纷,跟别人说我是党支部书记,没人认,说你连个凭证都没有,谁听你的。我们在组织部工作汇报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。
现在的罗湖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延勇,当时是科长,管流动党支部事务。他很快就给我们办好了工作证,盖上组织部的章。我出去就能名正言顺地亮出证件,说我是党支部书记,请你配合我的工作。
六
党支部刚成立,没威望,做什么都难。一个月后,老家达州市通川区青宁乡发生泥石流滑坡,一个2000多人的村子被冲了。虽然人没事,但是房子垮了,田地和牲畜都没了,人们的生活成了问题。
我将灾情汇报清水河街道党工委,他们给我们捐款15000元。我想着以党支部的名义,给受灾群众慰问,每户发一桶油、一袋米、受灾党员800块钱。
我在老乡住的小区楼下摆了个摊,登记受灾群众。我坐了三天,从早到晚,有老乡路过,我就逮着问。很多人不搭理我,只登记了60多人。结果发慰问品的时候,来了90多个人,米和油没有了,就折了100块钱给他们。这件事过后,老乡都知道,党支部确实能办事,威信就起来了。
早些年,因我们是“外来的”,有时会和本地居民起冲突。2009年,一个老乡去本地店铺买充电器。老板说没货,要等几天,老乡着急用手机谈业务,两边吵起来。结果人家叫来一伙人,把我们老乡狠狠地打了。挨了打的老乡,叫来一群老乡,把小区的巷子都给堵了,闹得很大,公安局也来了。
老乡问我怎么办,我说,你们听我的,我就出面调解,不听我的,我就不去。他们同意了。我到派出所和对方的人谈,待了一通宵。
我说,我们不要赔偿款,但你们要负责把被打伤的老乡送到医院去,医好为止;还要公开道歉,你们欺负了我们,要跟达州人道歉。赔偿款花了就没有了,但是道歉就能让所有人知道,是他们做错了。我不仅要给老乡争取权益,还要争点面子,叫人家不敢随便欺负我们。
对方没同意道歉,派出所按照规定拘留了他们。每天都有派出所的车开到楼下来,接我们老乡去医院检查、上药,大家都看着。我们的目的达到了,老乡也认可了党支部,凝聚力也起来了。
七
我们在清水河的老乡大约有8000人。党支部书记就像老乡的“大家长”,啥都要管。
老乡打零工的多,不签劳动合同,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欠薪。不久前,几十个老乡来我办公室,她们都在同一个清洁公司工作,干了一年,没拿到钱,总共被欠了10万多块的工资。
我打了清洁公司主管经理的电话,说我是达州市驻深圳办事处农民工维权站站长,我们有几十个老乡在你这里做工,一直没有收到工资,有没有这回事?他说确实有这回事,“不是我们不想给,是我们也没有收到客户的钱。”
我说,没有收到钱是你们的事,必须把工人的工资结了,她们要生活。拖欠农民工工资是“高压线”,不是小事。现在她们投诉到我这里来了,你们要尽快处理好,希望在明天听到你们的好消息,否则我们办事处还会找你们的。
当天下午,清洁公司出面解释,给老乡挨个打电话,说公司已经开会讨论了,三天之内会把钱给你们的。几天之后,老乡的工资全都讨下来了。
八
当支部书记没有工资。前几年,我会记账,一个月有几天是做党支部工作,不能干活的。后来太多了,我就不记了。
很多小的活,可能大公司不会接。街道里、社区里,键盘坏了、灯泡坏了,我都去修,随叫随到。有活我会叫上老乡,特别是年纪大的、困难的,外边不愿意雇他们。2017年,我开了自己的公司。去年工程量大概有50万,我能拿到10万左右,日子还过得去。
当年一起闯深圳的五个人,都分开了,有去宁波的,有到东莞的,有回老家的。老乡里面有混的好的,开公司,坐宝马,房子都买了几套,有的还挤在很多人的出租房里,有的病了,不想干了,就离开了。
现在我儿子和女儿都来深圳,成家了,我也有外孙了。儿子在做照明工程,女儿去厂里上班。他们这代人,和我们的路不一样了。
支部的年轻人吴彦成,去华强北修过手机,回老家卖过窗帘,现在又回来开餐馆,靠自己努力攒钱。以前我们做一天工才有一天饭吃,哪里想过这些,想到这么远。我在老乡里发展党员,也想他们能接我的班,继续给老乡办事。离乡不离党,流动不流失,希望流动党支部的党旗能一直飘扬。
来源:南方+客户端
【采写】夏凡
【策划统筹】赖武 高延勇 宫雪 吕冰冰 周宙
【出品】中共罗湖区委组织部 南方日报深圳新闻部
 扫码关注我们
扫码关注我们